召集有心人共同支持佛学院
民国七十九年搬回台北开香铺后,我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因而也接触到不少出家的师父,对于出家师父若是有任何的需要,例如:捐助车子或是座椅,或是盖佛寺时,需要认捐门或是窗的,我都会热心地找跟我一样有心的朋友一起赞助,因此知道我的师父们,都觉得我是一个热心且真心去“护持”佛法这条路的信徒。
就好像小时候,我受洗为基督徒,到我后来接触这么多的出家师父,我体会到不论任何宗教的神佛都是教导我们与人为善,神佛都是慈悲智慧,并像阳光一般,不会拣选评断万物,而是一律平等地照耀大地,但是只有人对人,会分你与我,会分派系,会分种族,也因为分别不同,寻求认同,而造成了纷争与伤害。
即使后来接触这么多的出家师父,或是接触学习佛法的师兄与师姐们,有些人真是令我非常的尊敬,有些人也让我受到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伤害,让我曾经一度怀疑宗教,怀疑佛法,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坚信神佛都是很有爱而无私的。
民国八十六年七月,经由卖我香的吴师兄介绍,而认识了我佛法上的父亲大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
当时他告诉我老仁波切是达赖喇嘛的经典老师,他的年纪非常大,我听完之后,对于仁波切或是西藏的密教,仍然没什么概念,因为当时我所接触的出家师父,都是显教的师父。
我第一次看到老仁波切时,是在一个吃饭的阳台,在地下室,吃饭的地方是隔成一间一间的和室,我一走下地下室的楼梯时,我感受到一股热气迎面吹来,(然而地下室的冷气,因为是七月天,冷度调得还蛮强的)同时我还听到绿度母的佛乐。
我坐下来时,我依然感受到那股热气的暖流,全身有种发电的感觉;当时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我隔邻的一桌,当我与老仁波切的目光接触的那一刹那,我感受老仁波切眼神中透出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慈祥的光芒,眼泪就不自觉地一直掉,想要停也停不下来,旁边的林师兄就给我们一张简介,是介绍老仁波切被中共关了二十一年的过程,我看了之后,眼泪又大量地涌出,事实上我虽然好像在听着师兄介绍老仁波切的事,但根本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后来莲品念佛会的林会长就带我去隔桌见老仁波切,我也不懂什么礼数,只跪在老仁波切前不断地流泪,这时老仁波切就非常慈祥地看着我,对着我笑,我也不知为何,就问在我身旁的师兄:“可以请老仁波切到我家坐坐吗?”
当时老仁波切的行程是安排得很满的,但是我还是直接问老仁波切旁的翻译 张老师,张老师就直接将我的意思以西藏话询问老仁波切,没想到老仁波切就答应了,我听了满心欢喜,用完餐之后,当老仁波切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我看到老仁波切的人好瘦小,而且背很驼,这时我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就在一旁偷偷地问翻译张师姐,她告诉我老仁波切在被关的时候,因为戴手铐与脚镣搬重转时,不小心从小山丘上滚下来,把背脊摔断了,才造成驼背。
之后,老仁波切以及五六个人就跟着我一起回家。当时我刚搬到延吉街,因为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我原本担心天这么热若是一开冷气,冷气的水又凸槌,滴到楼下去让邻居不爽该怎么办?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却下起雨,这场雨不大不小,要撑伞不撑伞都可以,地下只是有些湿湿的,因此回到家也不会太热,老仁波切就在我家看了一下,帮家里做了洁净的念经仪式,小坐了一会就离开了。
那天我看了老仁波切相关介绍,才稍微了解,年纪已这么大的老仁波切为了宗萨佛学院的两百多个学生的伙食生活费,从印度到台湾来弘法与募伙食生活费的款项,我就想既然这么辛苦,那么就尽我所能帮一帮老仁波切吧,因此我就找了当时念佛会的成员十七人,一个月两万元,持续三年护持宗萨佛学院学生的伙食生活费。
那天老仁波切来我家之后,我一整晚都睡不着,想着老仁波切,想着宗萨佛学院,一直到天亮,我就在佛堂上了个香,然后躺在床上睡着了,才一睡着,我就梦到一场很盛大的庙会,有很多人,地上还画了巨幅的彩色莲花与宝瓶沙图,还有警察,我看了这些警察,在梦中我还在想:是总统生日吗?今天又不是关老爷的生。梦中我还看到很多外国人,肤色偏黑(后来我才知道是印度人),同时还有很多台湾人,并且看到达赖喇嘛手牵着老仁波切,两人都面带微笑,边走边与身旁的很多人打招呼,达赖喇嘛还看了我一下,跟我挥了一下手;这个梦是在民国八十六做的,这个与梦境中一模一样的真实情景,在民国九十三年的十一月十九日真的发生了。(当天是宗萨佛学院大殿落成的典礼,一大早,当我走进会场时,我全身的鸡皮疙瘩如电流般麻透了我的全身,我整个人愣在那里,看着我梦中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周围的人纷纷跟我打招呼、说话,我完全没办法反应过来,同时眼泪直流。)
我从民国八十六年开始护持佛学院学生的伙食与生活费,若是每个月不满两万时,差额由我补满,满三年之后,又继续支持这项费用至今。
不先问困难大小,向着目标往前冲
当我认识老仁波切时,他尚未要盖佛学院,老仁波切在印度讲课,学生都是坐在空旷的操场上听课,讲课时也没有麦克风,学生的生活起居相当的简陋,在印度这么冷的地方,所有的学员洗澡是没有热水器的,因此老仁波切就跟他的老师蒋扬钦哲仁波切表示,他要到国外弘法三年,当时钦哲仁波切觉得老仁波切年纪如此大了,在印度安心教书就好,出外弘法是很辛苦的,然而最后还是抵不过老仁波切的坚持而答应老仁波切的愿望。
但是我认识老仁波切之后,我感受到他的那种如菩萨般的包容力与爱,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失去这一世的世俗父亲(我父亲在民国八十七年初二往生),但是我却找到一个佛法上的父亲,因此我从民国八十八年起大年初二我不回娘家过年,反而到印度去跟我佛法上的父亲过西藏人的新年。
等我到印度看了学院当时所拥有的校舍与居住的环境品质,我就发愿要协助老仁波切一起为宗萨佛学院的学生做更多的事,我是那种看准自己要去的方向就往前冲的性格,也不管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对我来讲,从小到大我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我学会了困难的作用,是要借此激发自己的创造能力,找到解决的途径,而不是用来逃避,或是借此放弃自己的方向与目标
然而,我在支持建佛学院的过程,却遭到我原本想象不到的挫败与困难。
四十岁的生日礼物 成了伤心之旅
民国八十九年的十二月二日,我晚上正在整理东西时,不经意中看到我桌上的罗盘,我望着罗盘就看到一幕景象,我穿着很多很厚重的衣服,站在国外的圣诞节街道过年,我看了就很开心。
到了十二月五日,有一对傅家的姐妹(我会认识她们,是因为她们的哥哥来找我卜卦,因此就跟他们兄妹成为不错的朋友,我就知道他们兄妹都在国外完成学业,英文都很好,我就想跟她们姐妹出去玩,我的破英文就不会是太大障碍。)告诉我,她们每年圣诞节都会到纽约与旧金山过节,并且购物,我一听就想到我在罗盘看的景象。
在当时我正在赞助一个布给喇嘛在旧金山念书,因为当时他要从印度去旧金山,请我支持他的学费与生活费,我就问他,他为何要去美国,他坚定地告诉我,因为他想完成学业,再回到印度辅助老仁波切办学院以及弘法,因此我就答应他,每个月都汇钱支持他的生活费,因此我也想要借此去旧金山探望布给在那边生活的状况。
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这辈子从未一个人出国履行,我想要跟傅家姐妹一起去纽约,当作是给自己的四十岁生日的礼物,我先生听了却跟我说:“我们的生活不太同耶!”
我先生讲这句话时,在当下我根本听不懂,虽然他不是很赞同我这次单独的旅行,但依然让我跟着对傅家姐妹一起去美国。
同时我也跟傅先生说,我要跟他的妹妹们一起去美国,他一听就反问我:“你真的要去吗?”我听他这样问,我就反问他:“你怎么这么说,不好吗?”他很直接地表示:“不好耶!”于是我就问他原因,他就告诉我,他的妹妹们不是很好相处的,但因为傅家姐妹常来我家吃饭聊天,我不觉得傅家姐妹是不好相处的人。
省钱为捐助名牌分阶级
出发之后,我们先到旧金山,傅家姐妹的朋友,就开车载我去找布给,接着布给也跟我们去旧金山吃了饭;第二天我们三个又跟布给喇嘛一起去逛街,但是我看了那些所谓打折的名牌,一样也舍不得买,并非我身边没有钱,而是我从小的生活环境养成我节俭的习惯,我宁可买“物超所值”的东西,也要把钱省下来给我的小孩家人,以及捐助给学院中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逛着逛着就看到一家内衣的店,换算成台币,我觉得符合我的“物超所值”的原则,因此我就买了几件,结果当傅家姐妹找到我时,傅家姐就用有些气急败坏的语气跟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要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不知道你躲在里面试内衣,害我们都很紧张!”
我听了就一直说,对不起,傅妹妹问我:“这种内衣你会买吗?”
我就自然地回答:“我买了几件。”
傅妹妹一听,脸就立刻地垮了下来,原来她们非常有钱,我买的内衣不是所谓的名牌,价格太便宜了,跟她们的财富与社会阶层不相称,因此她们从那一刻其就对我没有好脸色,然而在当时,我完全不知她们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
到了晚上,我们一起用餐时,由于我吃素,但是用餐的地方,并没有只有蔬菜的,我就点了鸡肉沙拉,把鸡肉分给布给吃,布给因为点了鸡肉咖喱饭附有面包,因此他就把面包分给我吃,傅妹妹看了这种情形,就跟我说:“其实接下来几天,你也不用叫餐,你只要吃我和我姐姐用餐点附的面包,这样一来你也不用花钱了。”此刻我才听出傅妹妹的讽刺之意。
接着第三天一大早,我们就飞往纽约。当我到纽约,走在华人街的街道上,真的非常的冷,这也是我第一次冬季到会下雪的国家,因此我没有带属于寒冷国家真正可以御寒的衣物,我只好把全部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但是走在街道上依然非常的冷,可是我却非常高兴,因为正如我在罗盘上看到的景象,我站在一个X形的路口角落,我的背后卖冰激凌,我的斜对角就是卖混沌的中国餐馆。
因为非常的冷,傅姐姐就提议先吃东西,问我要吃中餐还是西餐,我就表示,吃中餐先喝点热汤,于是我们就去卖混沌的那家店吃东西,但是傅妹妹是最讨厌吃中餐的,所以傅妹妹坚持不吃,我就点了一道面汤。
吃完之后,从十二点逛到下午四点多,这是我因为又冷,又渴,又累,觉得两条腿都不是我的,我就跟傅姐姐提议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咖啡,傅姐姐一听就说:“这边咖啡都很贵喔!”
我就说:“喔,没有关系。”于是就找了一个连锁的咖啡店,买了咖啡之后,她们就在看要吃什么样的蛋糕,傅姐姐就问我要不要也点一份,傅妹妹就自顾自地跟她姐姐说:“她买不起的啦,看她那个样子也知道。”
我心里就想,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也就是从此刻开始,我身上好像有毒,她们姐妹俩就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我就自己独自坐在面向街道的高脚椅上。
我看着窗外街道人来人往的人,突然我看到一个灰灰的外国男士,穿着燕尾服,带着黑色的高帽子,很想纽约十九世纪绅士的穿着,他用手隔着玻璃摸我的脸,还做鬼脸逗我开心,用表情告诉我,他知道我心里不快乐,于是我就把手放在他手放的玻璃上,我才一放上去,就觉得奇怪为何是温的,可能是因为太冷,让我的手冻僵了,之后他又做各种怪表情,我被他的表情逗得笑起来,这是我两天来第一次笑,接着我就听到从我身后传来对话,我听到傅妹妹说:“你看她有神经病,对着玻璃在笑!”接着傅姐姐就走过来说:“走吧!”
接着还是逛街,虽然那些首饰与名品都很漂亮,但我就是舍不得买,舍不得用钱。之后,回饭店就寝前,她们两姐妹都先洗完澡之后,我一进浴室一看,所有的大小毛巾都被她们用了,并且丢得乱七八糟,整个浴室还弄得湿淋淋的,这时我听到傅妹妹在外面敲门,并很大声的对我说:“那些毛巾我们都用过,你不会捡起来再用吧?”我就顺口说:“不会。”
隔天,我们出去逛街,看到新闻指出,有暴风雪要来,因此傅姐姐表示要回饭店整理行李,早一点飞回旧金山,原本二十九号下午的飞机,改成二十九号上午飞回旧金山。
赶回饭店整理行李时,我就到一楼打电话,我先打给 傅先生,当电话一接通时我就哭了,他就在电话那头说:“你怎么了?你受委屈了!”
当时我只是哽咽着回答:“嗯,大概我的东西都太贫穷了,我的英文又不好,我又不会讲英文!”
他就问:“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看不懂菜单。”
他就说:“看不懂菜单,就随便点,随便吃,不要为这个难过,回来再说,我就跟你讲不要去,你就要去”
挂了电话,我又打电话给我老公,当我正边哭边跟我老公讲电话时,傅妹妹却跟她的姐姐站在我身旁,傅姐姐对着我吼:“现在是怎样,你打电话给谁?你是不是故意打电话给我哥告状?”我就挂了电话跟她说:“我打给我家人都不行吗?”
傅姐姐又紧迫盯人追问:“你是不是打给我哥哥,说我们欺负你?”
我不想在旅馆的大厅里这样讲话,我就坐电梯回到房间,傅姐姐回到房间,依然对着我吼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在下面打电话哭!”
傅妹妹就走过来用脚踢我的行李说:“你现在给我讲清楚!”
这是我就蹲在我的行李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被她们行为表现吓坏了。
当我们一回到旧金山,傅家姐妹的朋友黄小姐开车来载我们,之后我们要住在黄小姐家,黄小姐发现我的脸色很差,就很关心问我:“老师,你都没有吃东西吗?”傅妹妹就在一旁说:“对啊,她都不舍得吃。”
到了隔天早上,黄小姐跟傅姐姐她们在打香蕉汁,黄小姐端了一杯给我时,傅妹妹就说:“不要管她,她是神仙,不用吃!”
那位朋友就问我:“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说:“大概我太贫穷了,我的东西都没有牌子,东西都舍不得买!”我说完又开始哭,我又说:“四十年来,我第一次想过自己的生活,买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黄小姐回台湾时也曾找我卜过卦,她就说:“其实她们就是这样。”
她告诉我,很谢谢我,上次她回台湾,我给她很多支持,她现在已找到一个真心的爱人,她过得很好。
她又跟我说:“你就把这一切当作,你跟她们有仇,这一世还完,朋友有的可以交很久,有的就是只能交到今天。”我听了这句话,就跟她说谢谢。
但由于布给喇嘛不知如何坐车与我会合,因此黄小姐很热心地表示,要先带我去布给喇嘛那,到时再去接我,这时傅妹妹就又很不客气地跟我说:“你要去跟喇嘛讲,我们欺负你,要讲你现在就可以去讲。”
这时黄小姐就对着傅妹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啊,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家?”
傅妹妹就说:“跟她在一起很痛苦。”
我听了就说:“对不起,让你们很痛苦。”
傅妹妹就说:“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给我坐远一点。”
由于她们仍然要逛街买东西,因此我就表示,我不想去,傅妹妹就说:“不行,我跟你不熟,如果我朋友家的东西搞丢了怎么办?”
黄小姐说:“你怎么这样讲人家,她是老师!”
傅妹妹就冷哼了一声,我就说没关系,我还是跟她们一起去shopping mal。由于我没有表,傅姐姐就把表借给我,约好一个小时后在中庭碰面,但我就坐在中庭假树下的座椅,心里边念着佛号。
在旧金山的机场,布给喇嘛来送我,他也发现我的脸色很差,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就大略描述一下我遇到的状况,边说又边哭,这时傅家姐妹就把布给喇嘛拉到旁边讲话,我就隐约听到布给喇嘛跟她们解释,我对他每个月以及学院在金钱上的赞助…..这时我决定先去处理我的行李,边处理时我依然边掉泪。当我上飞机一坐下之后,我就决定换位置,于是我拿起我的包包,这时傅妹妹就问我:“你要干嘛?”
我就说:“你们太尊贵了,太有钱了,我不跟你们坐在一起,而且我已经生病了,我怕把感冒传染给你们!”
我就到飞机最后靠厕所的空位坐下,一直哭到飞机起飞。
放下期望 重新出发
我边哭边不断地回想我在罗盘上看到景象,除了看到我站在纽约的街头外,我还看到很多水,那种水感觉是很伤心的水,这时飞机正好遇到乱流,我就想不会是我遇到坠机吧?如果是,我会很不甘心和这对姐妹死在一起,我回想从小我开始捡垃圾奋斗到四十岁,我觉得我受到一种因为阶级与金钱差距的污辱。人跟人的相处,外在真的这么重要吗?另外,我还想我是没有学好英文,所以才受到如此的待遇吗?
当我一回到家时,除了抱着我的婆婆与妈妈哭之外,我还到办公室拿起罗盘摔在地上,觉得罗盘为何不让我看清楚,我会经历的过程。
但是,我依然不明白我在罗盘看到的那滩水是什么意思?一直从纽约回来三年后,我才明白那滩水所要告诉我的事。
之后我在梦中梦到罗盘上的这滩水,这滩水在地上一直流,我在梦中一直想要找这滩水的源头,但又找不到,于是我就弯下腰,用手将这滩水捞起来,这滩水就变得如一般围巾的宽度,样子如半透明的粉丝,当我抓起来时,我就在梦中不断地哭泣,我是从梦中哭醒。
我还记得我在民国八十九年也是在印度过新年时,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布给喇嘛还俗了,我就从梦中哭醒,一早醒来我就打电话到美国跟布给喇嘛说我做的梦,他跟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还是告诉他,不论他要做任何决定,例如:要还俗这类的决定,请他都要事先告诉我。
民国九十二年我到印度宗萨佛学院过年,我就觉得大家对我的态度怪怪的,但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怪,当时我还去看布给喇嘛哥哥的小孩,这个孩子在达赖喇嘛的难民学校念书。后来我才知道布给喇嘛在美国还俗。佛学院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但不敢让我知道,怕我受伤。
我会知道这件事,还是我从印度回来,担任翻译的张师姐告诉我,当时我两是坐在计程车上,我一听我就在车上大哭,一回到家我就打电话给布给,我在电话这头很生气地跟他说:“你还俗了,就要诚实跟我说,不应该再拿我的钱,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接着就病了一个星期,一直发烧,完全没有办法卜卦,但我先生劝我,付出去的就付出去了。
然而我依然非常地伤心,只要听到“喇嘛”两个字,我就很害怕,也完全没办法想到老仁波切,觉得我支持布给喇嘛去美国,才会有这样的后果,让老仁波切失掉一个得力的助手。当我可以起床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到办公室拿起罗盘,先用力敲了罗盘,才问:“如果我没有支持布给去美国,他依然是一滩污污的水?”问完,我再看罗盘,依然是那滩令人很伤心的水。整整四个月,我都一直躲着任何喇嘛。
后来我就去见老仁波切,老仁波切很关心地告诉我,他听说我很伤心,走不出来那个负面的情绪,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时老仁波切却告诉我:他在被关的时候,也没想到未来会如何,只是一心念佛。老仁波切也告诉我,任何喇嘛来到他面前,跟他谈还俗的事,他都会很中立地跟想要还俗的喇嘛分析:“不论是要继续走喇嘛这条出世的修行之路,或是要还俗过世俗人的生活,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环境以及苦与乐,每一个当下做了选择,都要亲身去经历属于自己的旅程该经历的种种,以及要承担选择之后,所产生的种种结果,这都不是任何人可以去替代去经历与承担的。”
这句话让我放下了心中种种不平与困惑,我从老仁波切的这番话领会到,我选择支持布给喇嘛,这个选择就产生了一个因,就有我要独立去面对经历的旅程,与承担的后果,而不是抱着我个人期望的尺,去衡量别人,要按照我的期望去走。
经历这样的过程,结果如何,也是一个我要去珍惜与体会的学习之旅,也因这件事,我学会了付出就开心地去付出,并且我对人的爱的包容力,以及心量也变大了许多。
上车就不下车 终见好结果
我也回想到我在民国九十一年,我遭遇到一些人在言语上的攻击与误解,我觉得发愿要支持佛学院,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护持宗萨佛学院是我第二次发愿,第一次发愿是我姐姐过世之后,我再承天禅寺的地藏殿看到地藏王菩萨佛像,我就对着地藏王发愿,我愿意做地藏王的义工,我看着地藏王,我发现地藏王也在落泪),却让我觉得赚钱很辛苦之外,人性中的种种行为表现更让我身心俱疲,因此当我民国九十一年九月底去斋僧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时我最后一年来印度了,我不要再来了,这条路真是太艰辛了。然而那年我却在印度见到大宝法王,当我坐在大宝法王面前,我不解也好奇地问:“法王,做人很辛苦,为何您愿意一直转世再来?”
我一问完就哭了起来,大宝法王就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法王,发愿吧,发愿再来!”
大宝法王说:“当你开始这个旅程,当然中间会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下车,当你坐到终点,看看是什么结果,应该是好的结果,是你要的结果!”我听到这番话,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好,我要把我发愿的这条路走完。
接着我就问大宝法王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佛法上不退转?第二如何增福增慧?第三如何让我家人学佛,如何在命终的时候受佛陀接引,不坠地狱?
大宝法王针对我的三个问题回答是:“不断地发愿就不会退转;当你很虔诚地恭敬三宝时,同一时间,你就在增福增慧了;同时不断地发菩提心,一心不断念佛,这个菩提心不退转,就可以带着家人在命终的时候,接受佛陀的接引。”我还记得当时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被任何的攻击与误解以及赚钱的艰辛所打败。
因此当布给的事件发生,我见过老仁波切之后,我又再度地回想到民国九十一年大宝法王跟我讲的这番话,我就慢慢地从布给的这个伤心事件走出来。
感同身受 又吐又泄
我从支持佛学院所遭受的挫折中,学会挫折并不可怕,而是面对挫折时,我学会了什么,以及我选用什么态度,也因为老仁波切的身教,以及大宝法王的一席话,让我学会对人更有耐心与包容力,并更懂得珍惜每个来到我面前的人。
民国九十二年十月八日下午四点十三分刘美英来卜卦,她是要问她先生柳清木的健康状况。
那天中午,我吃得满饱,下午刘美玲一进来坐下,我就突然很反胃,于是我立刻跟她说:“请等一下!”
我就走出我的办公室,冲去厕所把我中午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光光,这是我卜卦这么久,从未发生的状况,当我再度回到办公室坐下来,还未等她开口问事情时,我已在她身旁看到一个画面,一个瘦瘦的,留着稀稀疏疏的三分头的人,我一看他是个病人,同时我也看到刘美玲在我眼前,用手不断地拍胸脯跟我说,她很紧张,因为从未卜过卦,我安慰她不用紧张,接着她跟我说,她要问她先生的状况,并将她先生的出生年月给我,一边解她先生已在九月二十六日住进马偕
医院,一边说,她双手还不断地捏着揉着一张卫生纸,她要我老实跟她说,她先生会不会……她还问完,我已明白她在问她先生是否生命之危,我就斩钉截铁地回答:“会,我跟你明白讲,你要有心里准备……”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肚子绞痛,我心里就想,这个人为何会让我又吐又泄?接着我看到刘美英的情绪很不稳,我就问:
“刘小姐,你家是不是有人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她听了还是拍着自己的胸脯回答我:“有!”她告诉我她哥哥住院一段时间,她自己也有,当她一讲完之后,我的耳鸣就好了,但,我还是受不了,得去厕所腹泻。
当我又再度地回到办公室,才一坐下来,我又看到她旁边,那个男的画面又出现了,我就跟她说,她先生是胃癌,她留着眼泪就问我:“有没有关系?”
我就反问她:“自古至今有哪个国王总统不死的?”
她依然很激动地跟我说:“老师,不要啦,不要啦……”
我就跟她解释,她先生不会很快死,但终究要面对死亡这个关卡。
这时我看了他们夫妇的八字,我就跟她说,他们夫妇的情感普通,他们俩常争吵,当她听我这么说时,她也承认,他们夫妇常为小事在争吵,然而当她先生生病时,她自己就反省是否因为对她先生的疏忽,才让他先生没有及早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她先生是在民国九十一年时常发生胃痛的现象,她先生常说要去看病,但都没有去看,
她也说要陪她先生去看,也没有行动,直到民国九十二年才去体捡,检验报告一出来,已是胃癌第三期进入第四期。
负面习性是因 胃癌是结果
刘美英就问我她先生为何会得这样的病,当她这样问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画面,画面中,她先生穿着短裤短上衣,拿着一把弯月形的镰刀,他看到任何动物就杀,就砍,甚至还乱砍树木与植物,而且一砍完,就很开心地一直笑,那种感觉是为了好玩。
我就跟她解释我看到的画面,并跟她解释这是他要承担的结果。当然,若是不相信佛法的人,不相信轮回的人,对于我所看到的,我所解释的,通常都很难相信,但我也不会勉强别人相信,因为一个人信仰任何宗教,都有属于其个人的缘分。
我就拿计算机算了一算,跟刘美英解释,她先生应该会活到六十六岁到七十二岁间,当然这个岁数不包括意外,意外包括病死和自杀,因为人有想不开的时候,当我解释时,她就问我,她先生会病死吗?我听她这样说,我就跟她讲:“那我们来打个卦好了。”
事实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有些犹豫,常常来找我的人不用卜卦,我都已经看到所有会发生的事情经过与结果,但来的人,都已准备好,常就等着问我:“我要开始了吗?我要开始了吗?”我就觉得不让来的人丢一下铜板,好像令对方觉得不满足,也会觉得不准。
于是刘美英一卜出来,我就跟她说,她先生的生命是在六十六岁最危险,然而我还是告诉她要有心里准备,因为她先生正要接受化疗,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鼓励她要支撑好自己,不要病人还未倒,自己就病倒了,她听我这样说,她确实很害怕,甚至到医院时,全身都会发抖。
我听了就跟她说,我就会尽量帮她,因为她先生要化疗,我就跟她说,若有机会要放生,我会通知她,她也表示同意。
我就教她,当要放生时,她自己要到市场去看,若被抓的是青蛙,蛇,乌龟等,因为被抓很痛苦,她要去买下来拿去放生,当把这些动物放生之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远去时,她要对着它们说:“愿放生的功德,回向给我这一世的先生柳青木,能够药到病除。”在这个过程,我帮她先生放生泥鳅一百只,麻雀八百只。
有缘相扶持 安抚死亡焦虑
刘美英这个过程,常来找我,一个星期可以打许多电话给我,有时候一天会打六到八通的电话给我,她非常的焦虑,不论是否要换医院或是医生等这类的大小事,都会打电话问我,在这期间我还告诉她,她先生回去工作一段时间,她先生确实在过完民国九十三年旧历之后,就回到原单位上班。
到了民国九十三年四月份时,她又来找我,她一进来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看她头上顶了无形的“两颗粽子”,左右各一颗,就好像古时候的人梳的包包头,我还以为我眼花,仔细一看也不是,确实是两颗粽子,她也发现我用奇怪的眼神看她,她就边拨整自己的头发边说:“我今天很没有精神!”
然而当她正在拨整她的头发时,她头上的两颗无形的粽子是不会动的,我又听她说,她都睡不好,晚上常睡不着,她问我她是不是生病了,会不会比先生先死,我就跟她讲,她是太紧张了。
大约是在六月十四左右,我正在山上八关斋戒中,刘美英就打电话上山找到我,她告诉我她先生又发烧了,她很担心,我挂了她的电话就去请教老仍波切,西藏人的占星学是很严谨而精准的,老仁波切就甩动他手上的佛珠之后,告诉我发烧没有关系,但这个人的病不容易好,我就问老仁波切:“这个人活不久,是不是?”
老仁泼切依然用很慈祥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也是快死的老头。”
刘美英认识我之后,只要一找不到我,就会很紧张,因此我会去闭关,或是去印度,我都一定要给她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她才会安心。
日子好难过 勇敢承担是解方
端午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大约是六月底,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先生的肚子发胀,我一听全身就有种不好的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在冒冷冷的气,我就问她:“你先生是不是吃粽子?”
她就反问我:“老师,你怎么会这么厉害?是啊!”
我接着又问:“他不是吃一颗,是吃两颗?”
她跟我说没错,我就跟她说,这两颗粽子会要了她先生的命,她一听就哭不停,我就跟她说,马上送她先生进医院,一到医院医生一检查,医生也跟她解释,吃馒头喝水撑死的故事。
她就一直请我救她先生,但是我依然要她做好她先生会死的心里准备。
这次她先生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到了九月,我去印度斋僧,喇嘛举行天麻除障的仪式,于是就去剪了白色、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的布,每捆布又剪成A4纸的大小,上面印着佛经的经文,挂在清净的高处,这些布一部分挂在莲花生大师出生的地方,一部分挂在学院。
那天,我们一行人去莲花生大师出生的地方,把这些印有经文的布挂起来,那天的天气,是雾茫茫的,我觉得好像身处仙境,这些布挂好之后,我就对着天空喊着需要祝福的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一地对着高高的天喊,但是喊到刘美英的先生时,我却突然忘记她先生的名字。
照理讲我应该是很熟悉她先生的名字,因为她一个礼拜都会打无数电话给我,而且我在印度时,她依然可以打电话到印度,辗转跟我通到电话,当时我就设法努力地想,依然想不起她先生的名字时,我就在心里想:惨了!
只好对着高空喊:“刘美英的老公,你药到病除了,我在这里祈福,你要坚强喔!”
我喊道这里,我心理想:唉,你都快死了,我还要你坚强!
于是我又对着高空喊:“菩萨,希望您能很顺利地接引他,最主要刘美英能够接受,不要崩溃!”
柳清木在住院期间,我请刘美英拿老仁波切的书及简介给她先生,柳清木看了就很感动,要刘美英捐了一万元捐助学院学生的伙食与生活费,而有一次我带着喇嘛到他们家去念经洒净,当刘美英外出处理事情时,我就谢谢柳清木捐助,帮了学院大忙,她却告诉我:“这只是区区小钱,我太慢认识仁波切。”
说的时候眼眶都红了,其中一个喇嘛也是宗萨佛学院的校长之一,就以藏文跟他说(一旁有懂中文的喇嘛帮忙翻译):“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修行,做人都有很多的辛苦,不管你今天的日子是好过,或是不好过,你都要去观想,这是你应该要去接受的。”我听了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这时柳清木还递给我纸巾,安慰我不要难过,而我看着他,发现他一直吞口水,强忍着不落泪,这是我问他:“你害不害怕?”他回答我:“我知道,我会做准备的。”
当我再次看到柳清木时,他是从医院来我的办公室,他做了化疗,头发是稀稀疏疏的三分头(就是刘美英第一次来卜卦时,我看到她身旁画面中他的样子),我就跟他说: “啊,你看起来很庄严,像出家人的样子。”
他点点头,同时我也看到他的右后方,发出两条腚蓝色与绿色的光。这次,他跟刘美英来跟我家的关老爷上香,没多久就离开我家。
我一直觉得我看到柳清木时,有种曾相识的感觉,我老是感觉要帮这个人的忙,但是最重要的大事却忘掉,除了在印度忘掉他的名字外,同时我也忘了柳清木的出殡时日。(我会用计算机算命,是因为民国七十九年十二月,我坐在办公室整理东西,我看到另一个我坐在我的左手边,拿了一个黑色的计算机正在算,我就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下,才发现另一个我,正在教我如何用计算机算命,因此我就很仔细地看着,当我看懂之后,另外一个我就不见了。那一年的圣诞节,就有一个人送了我一台黑色的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很准确,而且帮了我赚了很多钱,因此即使后来壳都裂开,我用封箱用的棕色胶带粘着固定继续用,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体面,但因为它是我的第一台计算机,情感很深,因而都舍不得丢掉,跟我比较好的朋友,每次都要我换一台,我都不愿意,期间后有人送我新的计算机,我很感谢地放在柜子里,依然还是用我这台用胶带粘补的黑色计算机,直到民国八十九年我才让它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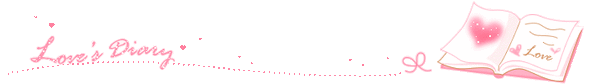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